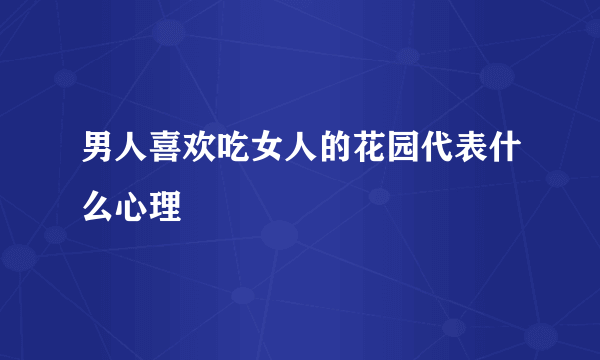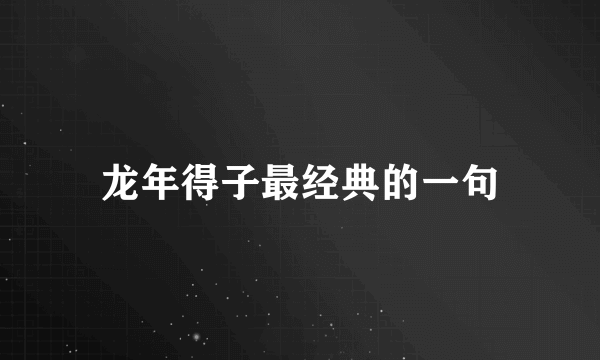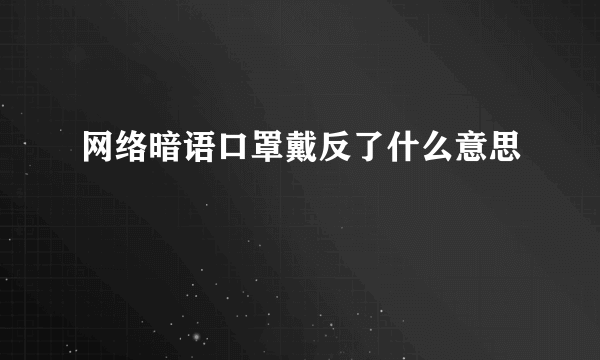阿累的《一面》原文
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: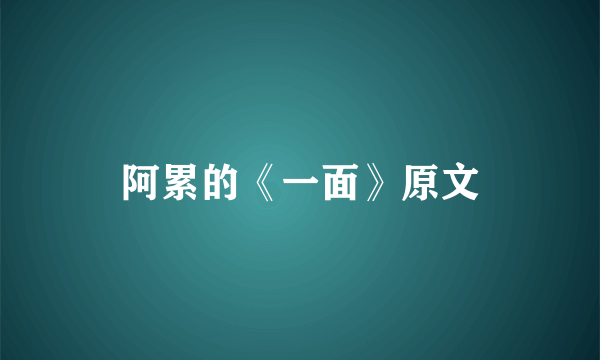
以下是阿累的《一面》原文内容:
1932年秋天,我在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当卖票的。
有一天中午,我去接班,天空正飞着牛毛细雨,离接班的时间还有半个钟头。我心想:到内山书店去吧,顺便歇歇脚,也躲躲雨。
走进书店,我一眼就看到了前几天议论过的那位青年作家——鲁迅先生,正站在书架旁看书。我立刻感到一阵惊异:一定!一定是他!那个头、那张脸;中年以上的年龄,精神很好,身体略胖,脸颊略微有一点儿圆,却又不怎么胖,也不瘦;两眼微斜向上,仿佛想望穿遥远的过去;两边的头发梳得很整齐,但是没有一根根竖起来,也不很平贴;牙齿黄得好像在牙齿上镀了一层金,一笑,嘴唇左右两边便各出现一个椭圆形的金圈。然而那一根根垂在双肩上的铁棒似的长发,一张消瘦的脸下端,差不多拖着一个小关公的胡子,那一天见他的时候,是刚由南洋回来,还是本就在那里住着的,我不能知道。
我们面对面地停住了脚步。鲁迅先生把面孔转了朝我,两道柔和的目光在我的脸上约略地扫了一通,忽然又带着轻看、好像说“我明白了”的样的微笑。同时,他的嘴角向上一扬,嘴唇两边的浓密的络腮胡子也跟着动了起来。
我结结巴巴的,欢喜得快要跳起来了,一定不会错!——这样的青年,这样的一个外貌,正是那天在车站里见到的那个人。
“哦!您,您——”
我结结巴巴的,欢喜得快要跳起来了。一定是他!不会错,一定是他!那个名字在我的心里乱蹦,我向四周望了一下,可没有把它蹦出来。
他微笑着,默认地点了点头,好像我心里想着要说的,他已经统统知道了一样。
这一来不会错了,正是他!站在前进行列最前面的我们的同志,朋友,父亲和师傅!憎恶黑暗有如憎恶魔鬼,把一生的时光完全交给了我们,越老越顽强的战士!我又仔细地看他的脸——瘦!我们这位宝贵的战士的健康,差不多已完全给没有休息的艰苦工作毁坏了。他带着奖励似的微笑,指着《毁灭》对我说道:“这书本来可以不要钱的,但是是曹先生的书,现在只收你一块钱本钱;我那一本,是送你的。”
我连忙接过来,打开纸包,是一本装帧并不漂亮的,纸已经黄了的小本子。我翻开看时,是赫胥黎著的《天演论》,译者和校正者都是鲁迅先生。这又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,别人不肯做,或不能做的事,他却能够做成功。他到底有什么法子呢?这个问题在我脑子里盘旋回绕,让我想又想,猜又猜,不解。
我看看那本很破的《毁灭》,再看看鲁迅先生那瘦削的脸,觉得他那笑容有些秘密,好像是从他的精神和心灵里涌出来的,绝不止是从嘴角边上发出来的。这时,我忽然记起哪本杂志上的一段访问记——
“哦!您,您姓什么?”
“我叫周豫才。”
“哦!久久仰慕!”我尊敬地道。
我非常高兴地、红着脸看了他一眼,他也微笑地看着我。
这种新来的敬意,让我更加难于开口,但终于鼓足勇气说了出来:
“那,那么,老师,我是——一个——工人……”
什么?我很惊异地望着他:黄里带白的脸,瘦得教人担心;头上直竖着寸把长的头发;牙黄羽纱的长衫;隶体“一”字似的胡须;左手里捏着一枝黄色烟嘴,安烟的一头已经熏黑了。这时我才注意到,原来鲁迅是一个矮小而结实的人。
“哦,你是一个——”他说,接着便讲述普通人都该读的书和一些关于读书的道理。
这一片段后来我一直记在心里。
在回来的路上,我看见挂在街灯下的旧社会,闭了眼睛,向前迈去。
“你要买这本书么?”他看了我一眼。那种正直而慈祥的眼光,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亲的抚摩——严肃和慈爱交织着的抚摩似的。
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起了一张嘴,向他问:
“多少钱一本?”
“一块钱两本,给你两本。”
他一面说着,一面拿起两本书送给我。
我看了看手头的一元钱,迟疑了一伙,终于不好意思地接过书,但是,书里还带着鲁迅先生的体温呢!
那夜一点过钟,我才回到家中,我高兴得几乎发狂。摸着那本书,仿佛上面还长着一层鲁迅先生手上的余温。
夜深人静的时候,天气又闷又热,躺在床上无法入眠,想要趁着深夜人静到窗前站一会儿,再回到床上蒙头大睡。窗外的天空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,下面是海边的沙地,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,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,项带银圈,手捏一柄钢叉,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,那猹却将身一扭,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……
这来的便是闰土。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,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。他身材增加了一倍;先前的紫色的圆脸,已经变作灰黄,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;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,周围都肿得通红,这我知道,在海边种地的人,终日吹着海风,大抵是这样的。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,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,浑身瑟索着;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,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,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,像是松树皮了。
我这时很兴奋,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,只是说:
“阿!闰土哥,——你来了?……”
我接着便有许多话,想要连珠一般涌出:角鸡,跳鱼儿,贝壳,猹,……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,单在脑里面回旋,吐不出口外去。
他站住了,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;动着嘴唇,却没有作声。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,分明的叫道:
“老爷!……”
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;我就知道,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。我也说不出话。
他回过头去说,“水生,给老爷磕头。”便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来,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,只是黄瘦些,颈子上没有银圈罢了。“这是第五个孩子,没有见过世面,躲躲闪闪……”
母亲和宏儿下楼来了,他们大约也听到了声音。
“老太太。信是早收到了。我实在喜欢的不得了,知道老爷回来……”闰土说。
“阿,你怎的这样客气起来。你们先前不是哥弟称呼么?还是照旧:迅哥儿。”母亲高兴的说。
“阿呀,老太太真是……这成什么规矩。那时是孩子,不懂事……”闰土说着,又叫水生上来打拱,那孩子却害羞,紧紧的只贴在他背后。
他就是水生?第五个?都是生人,怕生也难怪的;还是宏儿和他去走走。
宏儿听得这话,便来招水生,水生却松松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。母亲叫闰土坐,他迟疑了一回,终于就了坐,将长烟管靠在桌旁,递过纸包来,说:
“冬天没有什么东西了。这一点干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,请老爷……”
我问问他的景况。他只是摇头。
“非常难。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,却总是吃不够……又不太平……什么地方都要钱,没有规定……收成又坏。种出东西来,挑去卖,总要捐几回钱,折了本;不去卖,又只能烂掉……”
他只是摇头;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,却全然不动,仿佛石像一般。他大约只是觉得苦,却又形容不出,沉默了片时,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。
母亲问他,知道他的家里事务忙,明天便得回去;又没有吃过午饭,便叫他自己到厨下炒饭吃去。
他出去了;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:多子,饥荒,苛税,兵,匪,官,绅,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。母亲对我说,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,尽可以送他,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。
下午,他拣好了几件东西:两条长桌,四个椅子,一副香炉和烛台,一杆抬秤。他又要所有的草灰(我们这里煮饭是烧稻草的,那灰,可以做沙地的肥料),待我们启程的时候,他用竹竿捆缚了,自己背在肩上,向我们船舱走来。
我们终年忙着,竟不得一日闲暇。而这劳碌也并非为了我们自己,只是不愿违逆了父亲对于儿子的愿望。我从小时到现在,时时处处都要依从他,而且到处都碰着各式各样的钉子。小的困苦,几乎遇到了一个对手就要败一次,一把刀割下来,几乎每一次不留一点伤痕也要伤及灵魂。我从不怕困难,我可以受,大家都能受,只有精神会被杀害而杀不死,有一天会复活。
现在,在我的头脑里浮现出这样一个形象:一位在日本留学时曾以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志的青年,此时正站在昏黄的灯光下,用他那锐利如